8月4日下午从朋友圈看到许倬云先生仙逝的消息,自己还是有点吃惊。今年上半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访学。许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芝大有很深的感情。春节前,我给许先生发邮件,向他和师母曼丽恭贺新春,同时也询问他能不能利用我在芝大的机会去匹兹堡拜访他。他很快回了我邮件,说天寒地冻,路上行人稀少,他和曼丽大病初愈,刚从医院回家,让我不要去。想到许先生90多岁,身体虚弱,自己真不能将病菌带去,也就没有勉强。从他回复邮件的速度看,似乎与以前的许先生无异,我也就未担心他的身体问题。后来听几个与他们相熟的朋友说,许先生现在要用特殊的机械,将他从床上抱起来,再放到椅子上。外人可能感觉他很受罪,但许先生一生坚强,估计也不会是个大问题。许先生回邮件常常很快,说自己有一指禅的功夫。我曾亲眼见他用两个指头在键盘上将一个个字母敲出来,将邮件写好发出。作为一个先天有残疾的人,能有如此的定力与毅力,令人敬佩。
1998年,《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中先生为了报答母校的培养之恩,出资700多万美元,设立华英文教基金,支持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建设,推进这两所学校的发展,提升办学水平,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余先生193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49年8月更名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校址在四牌楼。1952年院系调整时,南京大学历史系搬到了汉口路,四牌楼变成南京工学院(改革开放后更名为东南大学)的校区。余先生因此将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同时列为资助对象。华英文教资金设立“华英学者”、“华英访问学者”等项目,奖助“华英学者”出国研究、补助教师或研究生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奖助“华英访问学人”来校教学、讲座,支持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补助外国学者旅费等,“走出去”与“引进来”齐头并进。该基金成立后,邀请了许倬云、杨振宁、刘遵义、刘兆汉等一批知名学者担任华英文教基金的评审专家,参与遴选相关的访问学人。
正是由于华英文教基金之事,许先生与南京大学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南京大学也因此聘请许先生担任特聘教授,为南京大学的发展献计献策。许先生建议南京大学仿照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做法设立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鼓励跨学科的研究。在这之前,经他推动,已在台湾大学设立了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从事人文、社会、科技各领域的基础研究,为这些领域的学者提供跨学科的交流机会。南京大学从善如流,很快成立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由当时的校长助理周宪教授亲自担任院长,是国内当时最早设立的跨学科人文社科研究平台之一。如今,高研院这一平台已经遍布国内各个高校。高研院成立后,南大在校内遴选了一批中青年学者驻院进行研究,我也荣幸与外语、新传、社会等学科的其他几位学者一起成为首批的住院学者。因许先生是高研院的创办人,这一年有不少时间在院内。因此,这一年内,我跟许先生就有了密切的接触。那一年,许先生除给我们讲座外,还找我们单独交流,同时牵线与台湾高研院开展学术会议。我们是第一批,第二批又有哲学、社会、中文、历史、法学等学者,两批一起到台湾大学高研院进行交流。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交流,使大家对彼此的研究有了了解,也互相学习了各自的研究方法,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己的视野。
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前馆长、东亚系荣休教授钱存训先生(1910-2015)是金陵大学文学院1932年的毕业生,国际知名的中国图书史研究专家。1952年院系调整时,金陵大学文学院并入南京大学,钱先生也就成为南京大学的校友。我在美国访问时,钱先生曾有将他的藏书捐赠给母校南京大学的想法。南大高研院成立后,正好缺一个图书馆,我牵线搭桥,在校领导和高研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高研院决定接受钱存训先生的藏书,并命名为钱存训图书馆。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询问许先生,能不能搞一个赠书仪式,同时开一个国际研讨会。许先生在芝大读书时,钱存训先生对他照顾无微不至。用许先生自己的话说,他五年读书有两年半在医院,钱先生和太太许文锦女士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一直感恩在心。自然,这一想法得到了他的大力赞成。他建议我搞一个国际研讨会,同时举行钱存训图书馆开馆仪式,并建议我与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合作,向美国的基金会申请经费。经过一系列的繁琐流程,2007年11月终于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中西文化交流与图书馆发展国际研讨会暨钱存训图书馆开馆典礼。在那个会议上,许先生深情回忆了他与钱存训先生的交往过程、钱存训先生对芝大图书馆的贡献等。接近百岁高龄的钱存训先生无法莅临,为会议特别录制了“对中美文化交流和图书馆工作的回顾”专题发言视频,派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的侄子钱孝文先生专程带到会议上来播放。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前主任李华伟先生、赠书中国基金会马大任先生、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时任馆长郑炯文先生、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时任馆长马泰来先生、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时任馆长周原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潘铭燊先生等多名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撰写了论文参会,共同见证了钱存训图书馆的开馆大典,在扩大了钱存训图书馆影响的同时,也为钱存训先生的百年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会议结束后,我奉命编校会议的论文集。弄好后,我邀请许先生做名誉主编,他也慨然同意,这便是201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为媒 沟通中西:中美文化交流与图书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钱存训图书馆开馆典礼会议论文集》。
许先生这些年来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出版,让我们这些后辈既敬仰又惭愧。他是无锡人,骨子里继承了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统。虽入籍美国,却对东方这片生他的国土满怀深情,始终忧国忧民,认为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但悲不见九州同”。他一直关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对民生的疾苦有深深的同情,希望能够改善民生。对美国的发展,也有他的认识。他写了一本《美国六十年沧桑:一个华人的见闻》,回顾了他的旅美生涯,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美国衰败背后的原因。我时常推荐给我的朋友看,让他们看看一个学者眼中的美国。
这些年,许先生也时常处于舆论的漩涡中。一是与李敖的纠纷。作为台大昔日的学生,李敖在台北起诉他,估计让他内心很受伤。二是著名的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曾说,如果他到芝加哥大学早几个月,许倬云就不能毕业。这次我在芝大,再次读了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感觉这中间既有学术观点的差异,也与何炳棣的个性、人际交往等问题有关。许先生的博士论文导师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曾与何炳棣先生有过龃龉,或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2019年,许知远远赴匹兹堡,做了对许倬云先生的专访,2020年春天作为“十三邀”中的一集播出,带给大家许多慰藉,使许倬云先生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中。之后,许知远再赴匹兹堡采访许先生,同样放在“十三邀”的系列中播出。在后一集中,许先生说:“今天的世界非常复杂也非常多事。我们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不能牺牲人格。我们什么都可以丢掉,不能丢掉自己。”这是一个95岁的老人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对未来大家、尤其是青年人的希望。他还说:“惊涛骇浪是人生不免……但(面对)惊涛骇浪,第一不能慌张,第二不能放弃。最要紧的是扎实自己,把自己的知识情感,都不要歪曲。同志相求,同声相应。能找到互相砥砺、互相切磋终身的朋友,就一辈子交下去。你自己本身就是榜样,你就会吸引别人。”这是许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遗言。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许倬云与南京大学“高研院”及钱存训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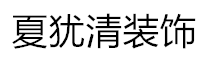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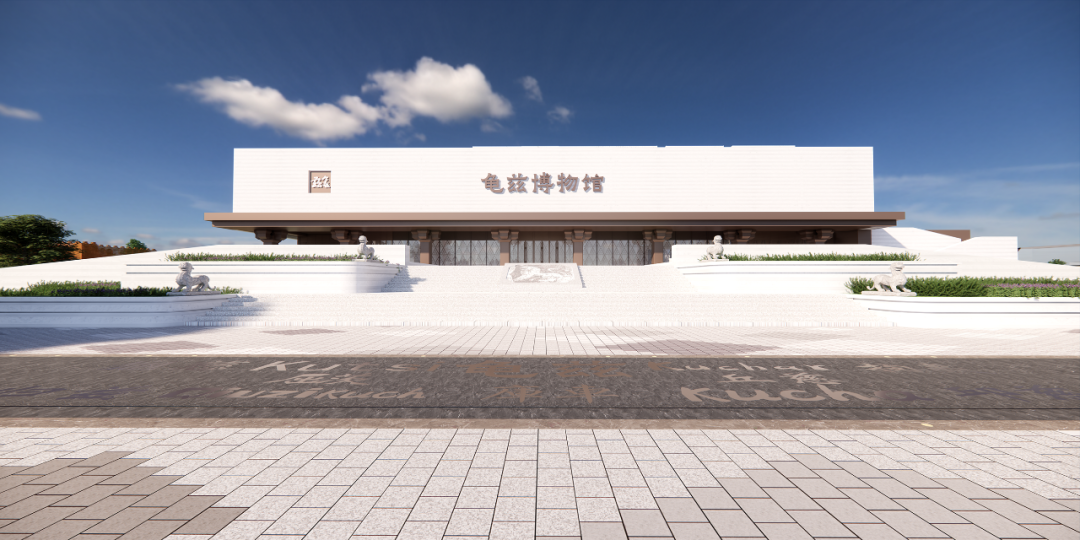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26
京ICP备2025104030号-26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