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小学起,“中华文明”和“灿烂辉煌”就作为一组绑定的搭配频繁出现在我所受的教育中。的确,这一点对每个中国人不言而喻。但少年时期的我从未认真“体验”过这种伟大性,未曾通过深入地阅读与探索,些许了解骨甲铜器的工艺,琢磨孔孟老庄的哲思,思索秦汉帝国的构架,感受韩柳文章的内蕴。而今我约略知道,若要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文明的伟大性展开探索,种种切面,尚需进一步融会贯通,加以统合,并置于更广阔的人类历史文明层面上予以理解。
这个中感悟,均是如今求学多年的我站在历史学家所谓“后见之明”(historical hindsight)的角度,回顾所得。当时的我并不觉得自己有这种体验上的缺失,也未曾料到,反而是对西方古典世界的研究给予了我认真探究中华文明的视角。欧洲自希腊罗马以降的发展轨迹,正好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完美参照。这类比较带给我们的,绝不应是单纯的某种特殊主义(exceptionalism),而是能够欣赏不同文明独特伟大性的能力,正如罗马通过高度自治的地方社群所维系的帝国,与秦汉通过中央集权下复杂庞大的官僚机构治理的帝国,都代表着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样态。正是两者间的相互比对,才能够更好地衬托出彼此的“灿烂辉煌”,从而产生一种交相辉映的效果;对我而言,这也恰恰是沉浸研习历史的诸多意趣之一。
如今的我们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已有足够的自信,上面这番赘言也只是我个人层面的一些体悟。即便脱离中国立场的主观语境,我身边的外国师友们也都一致认可中华文明的伟大,鲜少质疑之辞。然而,近一个世纪前的情况却迥然不同。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高傲与鄙夷杂糅的。知识分子们大体上仍深受黑格尔、兰克等人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偏见颇多。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永远停滞的民族;一些人认为中华文明古老而僵死,既缺乏历史价值,也缺乏写作意义;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与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等学者,则干脆提出中华文明可能是西方舶来的产物。社会层面,黄祸论喧嚣日上,美国颁发的一系列排华法案、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笔下的傅满洲皆为此例。或许难以想象的是,西方中国学研究恰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在19世纪的先驱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玛(W. A. P. Martin)、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人之后,沙畹(Edouard Chavannes)、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福兰阁(Otto Franke)们怀揣着真挚的热忱与好奇,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展开研究。他们的很多著述至今仍出现在中外大学的书单上,启迪着一代代志在研究中华文化的学子,而他们本身也成为西方对中华文明逐渐产生客观公允认识过程中几座最重要的早期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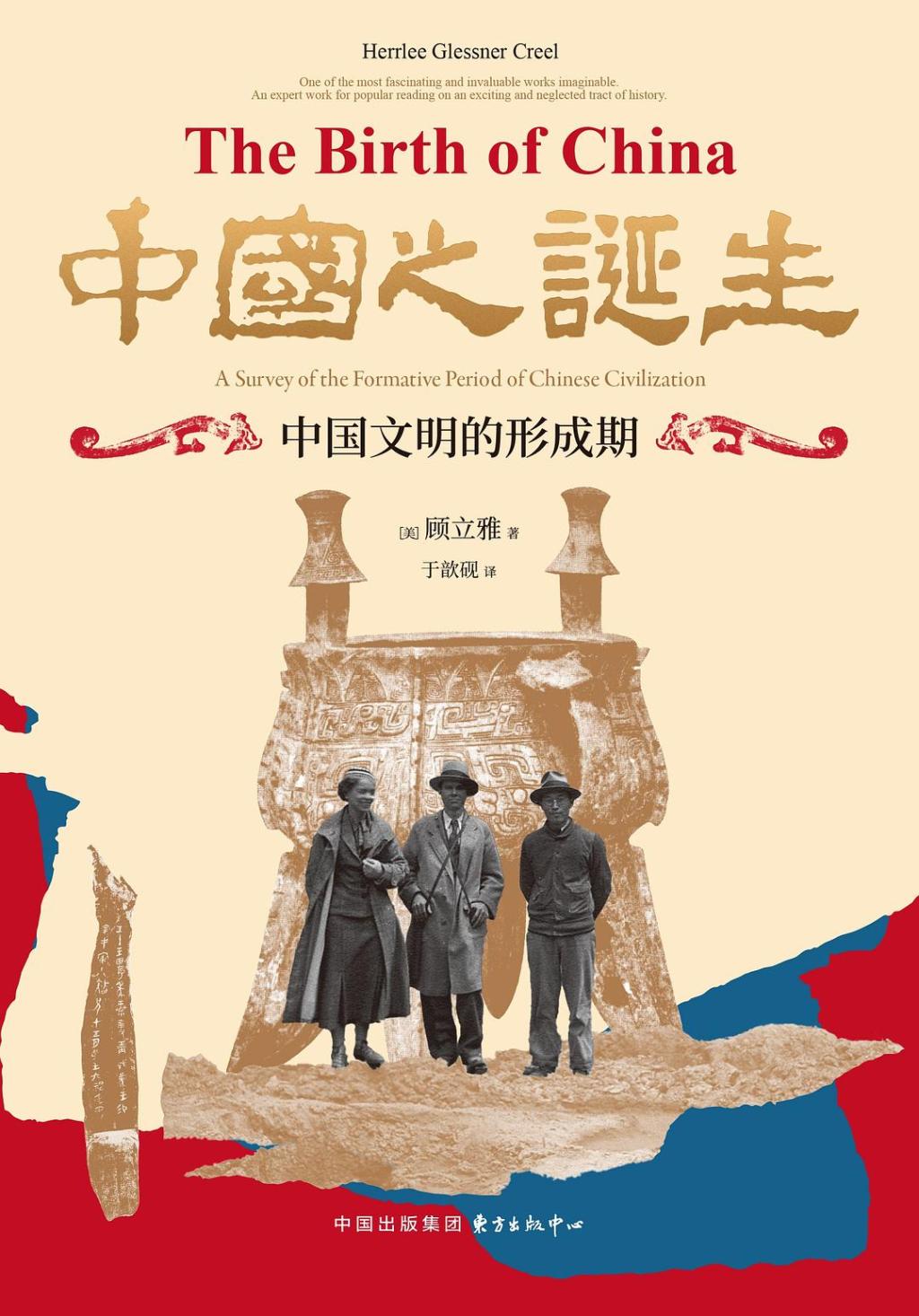
顾立雅先生就称得上是这些桥梁之一。论资辈,顾立雅比阿瑟·韦利等人晚了半代有余;他真正的学术巅峰期是在20世纪中后叶,即二战后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岁月,彼时新中国早已成立。之所以将其归入20世纪前期之列,就是因为这本1936年在西方出版的读物——《中国之诞生》。这本书的定位并非学术专著,里面的很多内容在今天看来可能并不新鲜,个别地方甚至会有些许谬误,但仍不应低估其阅读价值。首先,撇开主题内容不谈,这本书本身对于了解西方中国观的演变就具有一定意义。彼时欧美学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面对最新出土的考古资料的态度,乃至民国本身的社会风貌,从中均可窥得一二。其次,顾氏成此书之时,中国现代考古学尚处于初期开展的阶段。彼时,对商周的了解,仍多是依靠传世典籍中的记述。故此,此书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本新鲜的一手信息汇编。与主持安阳发掘的梁思永等诸多中国学人的友谊,使得年轻的顾立雅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新的一些文物发掘信息与初步研究。这些研究信息被顾立雅取之与传世文献互相参对,努力呈现出较为全面的古代中国图景,在《中国之诞生》中予以充分体现。后来,顾立雅的弟子许倬云教授在《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书中回忆,《中国之诞生》出版之迅速,曾令李济先生颇有微词:“我们还没有发掘报告,他已经写了一本书了。”不过此般迅速并没有以牺牲学术质量为代价:将近一个世纪后,我们回顾这本书时仍会发现,里面的观点大体上都是正确且颇具洞见的,这也令我们不得不叹服于顾立雅扎实的学术功底与敏锐的思维与洞察力。
然而在我看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顾立雅为中国“正名”所作出的努力和背后蕴含的人文关怀。就像毕安祺在序言中所提及的:
尽管与西方古代文明存在种种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无疑指向两者在史前时期某种程度上的接触——但大约三千年前在黄河流域存在的文化类型是典型且特征显著的中国文化类型。无论什么来自外部的思想、发明和技术,都已在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之前完全融入了这片新的环境。因此,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文化传播的中心,其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更早的时候在近东地区形成的另一个中心类似。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扮演的角色与巴比伦、埃及、希腊和罗马在西方地区所扮演的角色相当。这一事实,即在古代世界存在着不止一个而是两个进步中心,是顾立雅博士在他的新书中所明确阐述的诸多有趣观点之一。
在毕安祺眼中,这样的观点是“有趣的”。诚然,顾立雅就“中国文化西来说”作出的多方面驳斥算是本书的一条主线之一,但他对于消除傲慢与偏见的努力更体现在诸多微小细节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提到殷商墓葬中发现的人祭痕迹时,顾立雅并没有简单粗暴地谴责商人的野蛮,而是花了一整段告诉读者,这种行为曾广泛存在于不同的古代文明,甚至一向以“人文”(humanitas)著称的希腊罗马社会也出现过类似事件。通过商代建筑与希腊神庙之比对,西周与罗马的政治文化发展之比对,甚至青铜器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铸造工艺之比对,他温和而坚定地告诉读者: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轻蔑与鄙夷是滑稽而可笑的;中国人拥有不逊色于世界任何民族的伟大文明。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顾立雅是在学术探索的过程中,将华夏文明放在全人类的历史维度上,切身“体验”到其灿烂辉煌的。而他并不满足于此:通过这本书,他向整个英语世界的读者分享了自己的这一体验。我们无法量知究竟有多少西方读者是因为《中国之诞生》而开始慢慢改变对这一古老东方国度的成见,但我丝毫不怀疑它在促进文化理解与交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正如夏含夷教授在顾立雅的追悼会上所言:“我相信今日在座各位,由于阅读顾立雅教授《中国之诞生》而激发研究古代中国之热望的,我当非唯一。”
就算是我这样一个非科班出身、半路入门的中国史研究者,也素闻顾立雅大名。作为美国汉学界的元老,他一手把芝加哥大学打造成西方中国研究的重镇;而他的学问对我本人而言也有一层特殊意义:正是他1970年出版的《中国治国之道的起源·卷一:西周帝国》,启发了我博士论文的问题意识,让我以“原初帝国”(proto-empire)的视角重新审视周王朝,并将之与罗马共和国作政治演进层面的比较。1994年顾立雅先生仙逝之时我甚至还没出生,翻译此书,却让我感觉穿越时空与他相交相谈。那个蹬着自行车出入北平大街小巷间如我一般年轻的学者仿佛坐在我对面,神采飞扬地向我述说他心中无比璀璨的中华文明,邀请我陪他思绪共回商周之际。正当我着迷于他对古今中外的旁征博引,对经书典籍的信手拈来时,他又会突然穿插两句时事,把我拉到那个战火纷飞却大师云集的民国。甚至每当他提及古代地中海时,我都会有一种讶异的惊喜,仿佛他是在特意讲给我听。小普林尼在信札里的一番感叹,最能概括那段时间顾立雅和他的文字带给我的感受:“quanta potestas, quanta dignitas, quanta maiestas, quantum denique numen sit historiae, cum frequenter alias tum proxime sensi.”(我素知历史的力量之伟,尊严之隆,威仪之盛,神圣之至,最近亦深有此感。)这份相识感在翻译夏含夷教授所作中文版序言、顾立雅后来的回忆,以及友朋学生对他的追思之辞时,又加深了一层,就好似我也亲历了他的严格、慷慨、风趣,见证了他在生活中给周围带来的积极影响。2023年就在这样奇妙的时空错位感中飞逝而过,如今《中国之诞生》行将出版,心中又略怅然不舍,就好像自己要挥别一位故人。但同时我也充满期待,期待广大读者朋友们通过这本书也能获得同样的奇妙感受,也能结识那位对中国文明拥有无限热情的学者,并且也能在他的介绍下从更广阔的角度重新“体验”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我还记得去年初春凌晨两点写试译稿的心情。兴奋激动之余,我发现自己留学数载,外语没长进到哪儿去,母语的笔头功夫也没练出来,加之之前没有太多相关经验,很多话翻译出来觉得别扭,想改,却又投鼠忌器地怕扭曲了顾立雅一些细节处的原意。就这样摸爬滚打了大半载,总算勉强完成稿件,纵是之后又来回修改数遍,也愧于只能保证译文之“信”而未敢称“达”,更遑论有“雅”。故书中若有因小子才疏学浅而表达欠佳之处,万望读者诸君海涵。顾立雅此书主要是写给大众读者,很多地方未注出处,我在翻译过程中尽我所能进行了补充,以便读者参酌。以今日学术视之,顾氏书中个别未妥未尽之说,以及一些我认为有必要补充说明的信息,也都依愚见尽力注出,如有疏误,敬请方家赐正。
这一年多里,我得到了很多亲朋好友师长前辈们的帮助,此处囿于篇幅,无法一一致谢。感谢所有在这个过程中曾陪伴过我的人,你们对我而言意义良多。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的朱宝元先生,感谢他愿意委我以此般重任,耐心地解答我诸多技术上的疑惑,也感谢他和陆珺编辑对稿件的认真修改与为之付出的诸多心血。最后,尤其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家父在学术及译法方面的指点建议,感谢家母认真读完每一章节稿件并提出意见。此书非我所作,我本不应喧宾夺主,但还是想至少把这份译文献给他们:是他们对我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才让我得以在一个安心舒适的环境中一边求学一边完成这项工作。
2024年5月于爱丁堡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为文明正名——顾立雅《中国之诞生》译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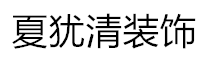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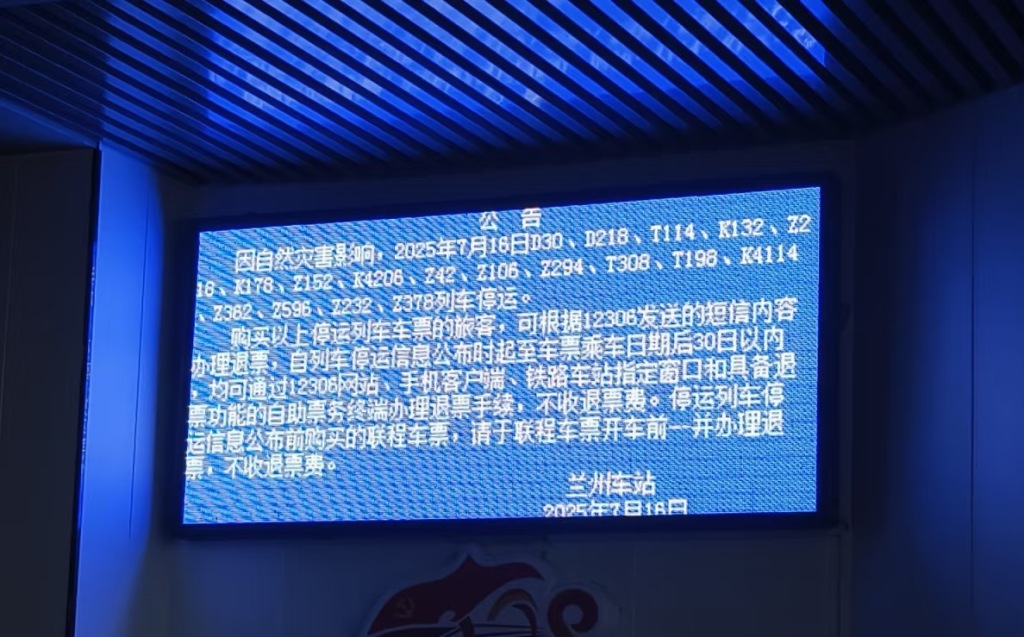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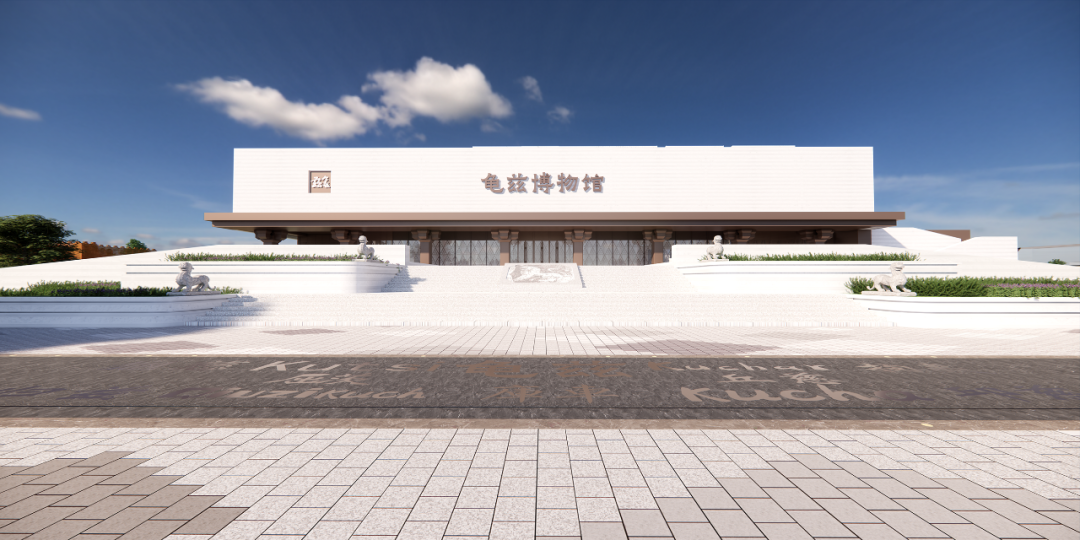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26
京ICP备2025104030号-26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